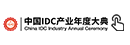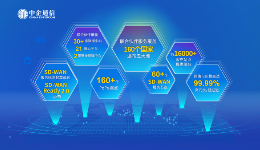无论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还是量子计算,这些引领科技行业未来乃至人类未来的前沿技术,IT业唯一的百年老店IBM仍都站在潮头,但这暂时还没有打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人

2015 年 2 月,陈黎明从英国石油公司跨界到 IBM 出任大中华区董事长。(资料图)
“现在,IBM可以停止再说‘转型’,该是‘加速’的时候了。”在1月18日的2017财年业绩发布会上,IBM董事长兼CEO罗睿兰(Ginni Rometty)说。
2017年四季度,IBM营收225亿美元,同比增长4%,终结了连续22个季度的收入下滑,这一长达五年半的业绩下滑屡屡被媒体和投资人问及,是笼罩在IBM头顶的一大阴影。
2017年全年,IBM战略转型业务增长11%至365亿美元,占总收入的46%,其中云计算业务170亿美元,规模已与微软(189亿美元)、亚马逊(175亿美元)相当。预计2018年IBM战略转型业务占比将突破50%,罗睿兰据此认为,转型已经“完成”。
IBM将云计算、认知计算(以人工智能平台Watson为代表)、大数据分析、移动、安全定义为战略转型业务,区隔于传统的IT服务、软件和硬件业务。
2014年5月,接掌IBM帅印两年后,罗睿兰发起了IBM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转型。她说,IBM看到了行业趋势的转移:竞争优势将来自数据和分析,云将重塑商业模式,个体活动将由移动和社交技术推动。
因此,IBM将重塑自我,转向更高价值、更高利润的市场,为客户、行业和IBM自己打造一个新未来。
2015年,她进一步清晰了这个战略:以云计算为平台,以认知计算为解决方案,专注于企业级业务的客户。她说,“现在我们既站在IBM的历史拐点,也站在技术的历史拐点。”
2017年,IBM营收791亿美元,毛利率47.4%,净利率16.3%;2013年,这三个数字为998亿美元、48.6%和16.5%。这一变化有市场原因,也与IBM过去几年主动剥离低价值资产有关,结果是收入减少,而盈利能力维持在较高水平。
业绩发布当日,IBM股价报收169.12美元,上涨0.47%,随后便震荡下滑,3月1日报收153.81美元。总市值1417亿美元,约为2013年底的80%。
2017年四季度,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再度削减对IBM的持股,出售3500万股,仅存200万股。
1993年出任董事长兼CEO的郭士纳(Louis Gerstner)领导了IBM的第三次重大转型,将IBM的收入结构从硬件主导调整为服务主导。郭士纳九年任期结束时,IBM收入比他上任当年增长了37%,市值增长了9.6倍,净利由亏损81亿美元转至盈利77亿美元,净利率8.96%。卸任后,郭士纳出版了著名的自传—— 《谁说大象不能跳舞》。
世易时移,罗睿兰能否让大象再次跳舞?
1月31日,IBM大中华区董事长陈黎明接受《财经》记者专访。他说,应时而变、不断转型是IBM的基因,正因为如此,IBM才能成为IT行业唯一的百年老店。IBM正在进行的转型是其107年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转型,转型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完成,更多转型成果将在加速阶段显现。
陈黎明强调,IBM是一家以科学研究、发明创造立足的公司,获得的诺贝尔科学奖数量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。如今是技术加速变革时代,人类正站在重大技术突破的当口,而无论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还是量子计算,这些引领科技行业未来乃至人类未来的前沿技术,IBM都站在潮头,这是IBM再次成功转型的基础。
转型完成了吗?
《财经》:从股价上看,与郭士纳的那次转型相比,资本市场显然尚未认可罗睿兰领导的这次转型。
陈黎明:股价起伏很正常,事实上媒体经常批评IBM过于看重华尔街的脸色,不过这也说明资本市场对IBM是有期待的。
郭士纳时代,IBM面对的主要是内部管理挑战,当时公司面临分拆问题。郭士纳否决分拆想法,改组管理流程和激励机制,革新企业文化,加大软件业务、引入服务业务,非常成功地实现了让大象跳舞。但目前这次的转型,难度之大前所未有。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商业环境、多重技术变革,以及远较当年强大的竞争对手。
IBM这一轮的转型始于五年前,当时定义转型目标时是说我们要向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移动、社交、安全这几个领域转型。随着人工智能重新兴起,区块链、量子计算的潜力被认识,IBM也当仁不让,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深厚的技术积淀。
《财经》:罗睿兰的用词是转型已“完成”,而不是转型已“成功”,这两个用词含义有何不同?
陈黎明:目前我们的营收,新兴业务占比已达46%,增速也快于传统业务,比如云计算去年增长24%,业务规模达170亿美元,仅次于微软和亚马逊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罗睿兰女士认为转型目标已完成。但是她下面还有一句话,要加速,要恢复增长,就是要在新赛道上加快增长,不再纠结于转型概念。
转型成功与否不是按新业务比例来定义的,不能说到了60%就成功,50%就不成功,我们的传统业务还有非常多的客户,比如大型主机、高端服务器、存储,这些对客户都是不可或缺的,我们依然要提供好产品和服务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《财经》:IBM前几年虽然营业收入在下降,但是毛利率在提升或者维持。2017年营收和毛利率都在下降,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讨论过?
陈黎明:具体的财务问题等我们的2017年报出来后都会有解读,从我这个角度来看,IBM未来发展战略非常清晰,就是以云计算为平台,认知计算为解决方案,专注于企业级的客户。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奠定了良好基础,正在进入加速发展阶段。
IBM还能留在舞台中央吗?
《财经》:和IBM同时代的企业,除了微软,其他基本上都光芒黯淡了,比如曾经如日中天的惠普、戴尔。张瑞敏有句名言“没有成功的企业,只有时代的企业”,意思是跨时代成功的企业非常罕见,IBM还能留在舞台中央吗?
陈黎明:微软1975年创办的时候,IBM已经64岁了,IBM可以说是IT行业唯一的百年老店。你刚才谈到股价,股价起起落落,真正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它能否基业长青。
IBM的百年史就是一部转型史,转型意识已是IBM的基因。IBM最初并不是家聚焦计算的科技公司,除了打孔机,它还做磅秤、切肉机和咖啡机,差不多也是什么赚钱做什么。后来老托马斯·沃森重新定义了公司,专注于计算,当时的计算当然就是机械打孔机。
上世纪40年代,电子计算机出现了,老沃森并不理解电子计算,但他不阻止儿子小沃森尝试。1956年-1964年,IBM花了50亿美元研发出大型主机System/360,相当于今天差不多400亿美元,超过了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投入,这真是一场豪赌,但IBM赌赢了,自此主导大型机市场至今。
然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个人电脑兴起,IBM一度落后,但很快再次主导,我记得自己刚接触电脑的时候,PC就叫IBM兼容机,IBM定义了当时个人电脑的标准。
再往后就是90年代郭士纳那次广为人知的转型,当时IBM濒于破产和分拆,但郭士纳再次引领了行业潮流,就是IT服务和电子商务。这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彭明盛(Samuel Palmisano)时代。彭明盛致力于提高利润率,退出低价值业务,提出智慧地球概念。到今天就是罗睿兰女士引领的这次转型,以云计算和认知计算为核心。
所有企业的转型都有重大诱发因素,在我来看,这些因素第一是科技变化,二是商业模式,三是政策环境,四是自身管理,比如郭士纳所引领的那一次转型,我认为就是管理模式所诱发的一次重大企业转型。所有的重大转型都是非常痛苦的过程,因为你要做组织架构的变革,运营系统的变革,人才的变革,企业文化的变革,哪一项变革都不容易,尤其是涉及到个人的时候,要么你是转型的一部分,要么你就被留在岸上了,因为这个大船是要走的。
正是因为IBM有转型的基因,所以我们对转型充满信心。从企业管理的角度,我想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:一是不要把企业定义为某项产品的企业,否则产品没了企业就没了;二是不要沉溺于历史,你的历史无论多辉煌,那都是翻过去的一篇,要着眼未来;三是要敢于向未来下赌注,无论技术还是商业模式,选定方向后就要坚定不移地执行。
《财经》:时代变迁的节奏在加快,能够生存下来肯定需要不断转型,但是生存下来和舞台中心是两个概念,比如柯达,重组之后仍在运营,可已经没多少人想起它了。
陈黎明:IBM的自信不仅来自转型基因,还来自科学基因。我们有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,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;有6位图灵奖获得者,相当于计算机行业的诺贝尔奖;有八九十位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,赢得5次美国国家科学奖,10次美国国家技术奖。
2017年,IBM的专利数达到了9043项,再次拿到美国专利冠军。其中,1400项是跟人工智能有关,1900项是跟云计算有关,1200项跟网络安全有关,IBM的发明创造来自于四十几个国家的8000多位科研人员。
IBM目前是唯一可以把20个量子位的量子计算服务挂在网上的公司,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使用,同时也推出了50个量子位的原型。我们去年发布了5纳米芯片技术,发布了单原子存储技术,这些技术都有着巨大的商业化应用前景。所以,回到你关于舞台中心的问题:在相当多的重大前沿科技领域,IBM毫无疑问依然是聚光点。
如何与总部相处
《财经》:让我们回到中国市场,去年中国市场的表现怎么样,转型节奏与整个公司同步吗?
陈黎明:因为IBM的财务纪律,我无法透露具体经营数据,但我们的战略转型业务占比和集团是基本同步的,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。2017年大中华区的业务可圈可点,比如云计算,IBM私有云进展非常好,总部也很认可。公有云方面,我们总体还是在稳步推进。在服务器、硬件系统方面,跟浪潮的合资这一年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。另外,跟中国电子在Watson健康这个领域的合作、跟百洋在Watson肿瘤和基因方面的合作,也都是我们这一年的亮点。
《财经》:令人忧虑的事情是什么?
陈黎明: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,发展这么迅速,创新的活力这么强,IBM在中国的业务不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,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胆子更大一点,步子更快一点,抓住这一次的发展机遇。
《财经》:听上去不是担忧,而是希望总部给中国市场更多的资源。
陈黎明:能够得到总部广泛的认同和支持,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比如当初大中华区提出“3+3”战略,是自己搞的,而现在我们新业务规划是跟总部联手去做,这就会让内部统一变得更容易一些。
《财经》:总部有没有抱怨过中国市场的投入产出不相匹配?我们听到一个说法,大中华区营收占IBM总营收的比重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体量不相匹配。
陈黎明:具体数字我无法透露。IBM在中国的业务,早些年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发展,这跟当时的政策环境、市场环境以及客户对于我们的需求密不可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本土企业也在成长,市场环境、政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这种情况下,增长的势头不像以前那么迅速,这完全可以理解。从我们的角度来说,必须在新常态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,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,总部对此也很清楚。
《财经》:如果能从总部争取更多的资源给中国市场的话,您觉得哪方面的资源是最需要的?
陈黎明:资源需求取决于业务发展,当业务发展确实有这样的资源需求,比如某项业务前景非常好,需要资源就顺理成章。假如这个业务成长性不是很好,去要资源也会很纠结,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。
《财经》:有时候是不是也是鸡生蛋、蛋生鸡的关系,一方可能会说你先做出业绩再给你资源,另一方觉得你不给资源我怎么做出业绩?
陈黎明:不能完全这样讲,比如医疗健康这类新兴领域,前景非常好,以前基本是空白,我们现在要把市场创造出来,这时候资源是能得到保障的。关键是你要有说服力地把这个市场前景展示给总部,这是最重要的。
《财经》:大中华区EMT(执行管理团队)里的11个人是怎么构成的,大陆人几个,美国人几个、香港台湾人几个人?
陈黎明:还是华人居多,大陆的、香港的、台湾的加起来远超其他地方的。当然我们在选择EMT成员的时候并不刻意考虑来自什么地方,因为IBM本身是追求多元与包容的公司。倾斜政策是有的,比如女性高管比例,在我们这儿有考核指标。但政策倾斜主要体现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,选拔人才时是不考虑这些因素的,完全凭能力、凭实力。
《财经》:EMT成员是大中华区就能决定的吗,是否需要报美国总部批准?
陈黎明:我就可以决定。
《财经》:我们听到一个说法,您刚来的时候作为第一个本土大中华区董事长,还是蛮提振士气的。两三年之后,EMT团队的美国人、香港人、台湾人的比例又在上升了。
陈黎明:这个现象不存在。本土化是我们的人才战略,本土人才在这两年得到的提升是前所未有的。
跨国公司在中国玩不转了吗?
《财经》:您刚才提到中国本土公司这些年进步非常快,其实不光是华为、浪潮、BAT这样的大公司,在IBM战略转型业务领域里的初创公司势头也很猛,它们与跨国公司相比,技术差距在缩小,经营方式也更灵活,对此IBM有何应对之道?
陈黎明:中国公司的确成长十分快速,这既是因为有一批优秀的创业者,也得益于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,简单来说可以用政策红利、人口红利、城市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来概括。IBM也从中国的这种巨变中受益很多。中国企业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,这个现实跨国公司必须要面对。同时,作为有百年历史的跨国公司,在IBM合规是第一要务,这是我们的价值观,做任何一张单子都要合规,这方面我们是零容忍,绝对没有什么灵活性。
《财经》:早先的中国市场,IBM在技术上有绝对优势,哪怕销售上没有任何灵活之处,客户也得买IBM的东西,现在还有这个底气吗?
陈黎明:过去别人说IBM的员工从背影上都能看出来,那个时代今天不复存在了,不复存在的很大原因是本土企业在很多领域可以跟IBM正面竞争了,这个过程中,我认为包括IBM在内的跨国公司为中国市场做了很多贡献。如果没有改革开放,这些技术不可能进入到中国来,本土企业也不可能迅速发展。
尽管如此,在我们刚才谈到的大型主机、高端存储、区块链、认知计算、量子计算等很多方面,毫无疑问IBM的技术依然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优势。另外不要忘记IBM强大的服务团队,一个大型计算系统背后仰赖的不仅仅是计算机本身,还有卓越的服务。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如果宕机,都是以秒来计算,不是很多公司都能确保银行运营的平稳、安全、可靠。
此外IT公司中没有几家比IBM更懂得行业,我们服务行业这么多年,在行业知识上的积累不是哪个竞争对手短期内能具备的。比如搭建一个云平台并不难,你愿意花钱,给了你证照,你就可以搭起来。但搭起来以后如何让它用起来,数据回来后能不能理解分析,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,这就是IBM的优势所在。
《财经》:但是我们看到IBM的人才不断流失到本土公司。
陈黎明:所有跨国公司都存在人才流失问题,但是相比之下,IBM的人才流失在可控范围之内,因为我们的创新、我们的专业知识、我们的历史文化还是非常留人的。IBM每年都招聘很多毕业生,社会上也招聘很多,我就是外面来的,所以IBM也引进很多人才,对此我们没有太多的担心。
另一方面,人才流动对社会而言不是坏事,中国以每年10%的平均速度增长了30年,成就了一大批本土企业,这些本土企业需要人才,而跨国公司是它们重要的人才来源。所以说,跨国公司也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,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。
《财经》:在当今这个剧变时代,对人才的定义有无变化?
陈黎明:过去讲“T”型人才,有一定的知识面,但更重要的是某一个行业的专业知识。现在是“π”型人才,既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,比如程序员、架构师,同时对另一个或更多行业也有深度了解。“π”型的跨界人才现在远远供不应求。比如“跨国”,这对很多本土企业也非常重要,因为它们要“走出去”。 “跨行”,现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,尤其是IT行业,要渗入到各行各业,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跨界人才。
《财经》:根据您的观察,中国好的企业与美国好的企业相比,差距是什么?
陈黎明:本土企业的进步毫无疑问可喜可贺。总体来讲,本土企业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多,目不暇接,但在硬科技方面还有差距,包括基础科研和应用科技。
《财经》:您如何评论中国新四大发明(高铁、支付宝、共享单车、网购)这种说法?
陈黎明:讲新四大发明针对性太强,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创新模式。我们过去的创新思路,叫“引进-消化-吸收-再创新”,在发展早期阶段这肯定没错,历史上很多国家都走了这条路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国力的增强,是不是继续这种模式值得思考。“引进-消化-吸收-再创新”脱离不了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,我们应当加大原创型创新,加大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。中国的科研投入很庞大,但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。应用开发要靠基础科学拉动,当然这个周期比较长,但是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可持续。
《财经》:从商业角度讲,IBM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,市值还不到1500亿美元。阿里巴巴、腾讯没有什么发明创造,5000亿美元的市值。您怎么看这种落差?
陈黎明:市值是一个重要衡量指标,但我们看看历史,如日中天但昙花一现的新兴公司,辉煌良久但一步踏错、步步踏错的老牌公司,数量都不少。基业常青的公司才是真正卓越的公司,这需要时间来验证。